你知道王安石为什么背负骂名吗?我不知道。没关系。我来告诉你什么有意思。
《易经》里说“一比一叫变。"门的开合是变化,月亮的阴晴圆缺是变化,大海的潮汐也是变化。理论上讲,灵活变通会扭转局面,但一旦涉及到政治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,从战国时期的吴起改革到清末1898年的戊戌变法,都很少成功,“没有一项改革像王安石的改革亡国”这一耻辱一样不堪重负。
 & quot;安史之乱天下”如果是这样呢?
& quot;安史之乱天下”如果是这样呢?
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,最后宋神宗死于元丰八年,又称“熙宁变法”。这次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,丰富强兵,挽救宋朝的政治危机。财务管理”,团结军队”为中心,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,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运动。
据史书记载,变法那年,词圣和任绪安两位后妃,放声大哭,向宋神宗哭诉:“安史之乱天下”。所以,应该算是宋朝最有魄力的皇帝宋神宗开始犹豫了。所以,王安石变法在上帝统治时期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赞誉。
王安石在宋徽宗统治时期受到最高的赞扬。当时各地接连发生起义,包括最著名的梁山好汉起义。此时,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被他的接班人、对手、旧友司马光彻底推翻,但宋徽宗肯定了王安石变法所带来的变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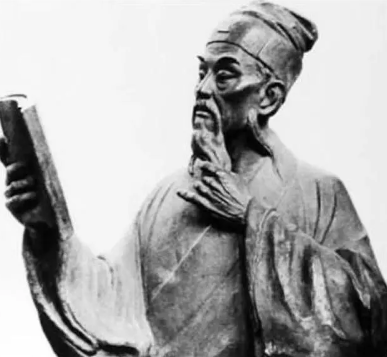 可惜好景不长。宋徽宗之子宋钦宗继位,上台后不久又推翻了王安石。然后,次年,北宋灭亡。"安史之乱天下”这时似乎得到了证实。
可惜好景不长。宋徽宗之子宋钦宗继位,上台后不久又推翻了王安石。然后,次年,北宋灭亡。"安史之乱天下”这时似乎得到了证实。
那么,王安石做了什么?
从今天来看,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是值得肯定的,比如青苗法。他用目前主流的金融手段——借贷来支持农业的发展。后人对幼秧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,南宋时甚至有不少人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。
当时北宋的官方利率是每半年20%~30%,一年的利率是40%~60%。乍一看,利率确实很高。但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是100%~300%,是官方借贷的几倍。
这样的话,青苗法应该是支持的,但为什么是这样的评价呢?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官员会强迫农民借钱,而我们古代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,农民不愿意冒险花明天的钱去做今天的事情。此外,官方借款利息的增加并没有帮助农民获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本金。
表面上是“三冗”实际上是农业问题没有解决,导致了北宋的衰落
这个结果不是王安石的初衷。他的初衷是通过官方借贷抵制民间借贷,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;另一方面,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。只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,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,所以在政府借贷出现之前,民间借贷是如此“繁荣”。
但王安石通过官贷限制民间借贷,触及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。青苗法被地主阶级阻挠,地主阶级反过来压迫农民,全国人民哀悼。王安石不得不背负被千夫所指的骂名。
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,王安石想“压低地主的利益”。还富于民,还国”。但他忘了,皇帝是当时最大的地主,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障碍。如果他想改变农民的现状,他必须跨过皇帝的“大山”,但在古代这是不可能的。
腐朽的根挖不出来,做什么都是徒劳。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症结就在这里。宋神宗可能已经发现了它,但那又怎么样呢?因为他烂了《魔戒之一》他改变不了现状,更不能推翻自己。
现在提到北宋,我们更愿意用“三冗”来形容当时的社会背景,其实这种说法很差!"“三冗余”只是表面的东西,虽然“多余的士兵”,多余的官员,多余的开支”国库的开支增加了,但如果国库充足,北宋可以负担。除此之外,“三裁”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吃饭就业问题。
只有农业是国家的基础,一切问题都归结到“田”身上,要解决农民问题,就要减轻农民负担,发展生产。所以王安石变法陷入了无限循环。地主阶级不愿意割自己的利益,农民没钱种地。政改如何才能成功?国家如何繁荣稳定?
 此外,王安石变法也涉及严重的政党竞争。
此外,王安石变法也涉及严重的政党竞争。
政党斗争动摇了国家的基础
王安石变法开始后,参与变法的官员被称为“新党”,不参与变法的官员被称为“旧党”,这在客观上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平衡。在此之前,党派之间也有斗争,但都围绕着一个共识:无论哪个党派执政,都不可能报复和容忍反对的声音,但王安石代表的是“新党”破例。
在宋神宗的支持下,王安石把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全部赶出首都。这不是王安石的道德问题,而是国家正义的考量。他首先忠于国家,其次忠于政权。但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像他一样“天下先有忧”,新党为了保证变法能够实施,处处针对老党,但老党往往是出于报复,回到高位后,新党都会被赶出首都。两派斗争不倦,由此挑动了北宋。
 党争在后期政权中愈演愈烈,最终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。新旧党有显著差异,新党注重效率;老党看重道德,爱说空话、谎话;新党听皇帝的话,老党喜欢批评皇帝,这是相当“依仗旧卖旧”的趋势。
党争在后期政权中愈演愈烈,最终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。新旧党有显著差异,新党注重效率;老党看重道德,爱说空话、谎话;新党听皇帝的话,老党喜欢批评皇帝,这是相当“依仗旧卖旧”的趋势。
这其实就是新旧党背景造成的差别。新党只靠王安石逐步走上政治舞台,是政治新秀;但老党存在了几千年,权力根深蒂固,不可动摇。它土地面积大,属于既得利益者。
那么为什么新旧党会有那么多不同呢?当然,因为新党的政改政策触及了老党的利益,所以强烈反对。但从皇帝的角度来看,新党作为后起之秀,并不强大,也不容易掌控。所以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场景:宋徽宗年间,他重用新党,肯定王安石对变法的贡献,但是没有用。
所以王安石变法无论从治国之道还是思想建设的角度,都不利于北宋的发展。前者动摇不了根,永远没用;后者为激烈的党争开了先例,使作为主要行政力量的公务员逐渐腐朽,最终腐烂到骨子里。
然而,王安石是“幸福”的。
庄子曾说,终极的幸福在于列子的物我合一。所以王安石是幸福的,因为无论他得罪了多少人,比如苏轼因为断送了仕途而多次被贬;司马光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知己成为头号对手。后来,王安石甚至提出了“亡国论”,“天下大乱”但无论改革阻力有多大,批评家的声音有多尖锐,王安石仍然可以不忘自己的首创精神,在时代的洪流中逆流而上。
王安石是一个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,是一个先天下之忧的人。他从来不把个人利益得失作为改革的依据,这与后来的改革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。
从实现人生理想来看,他比大多数“一辈子没出过一份报纸”的人都幸运。王安石有过一次机会,从后世的角度看,他的改革是成功的,大概就是“生机”吧。但作为政治家,王安石的变法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。他性格上的执拗,他那种不能真正动摇社会本质的政策,从根本上决定了“改革”的道路是漫长而漫长的。
 黄是谁?为什么他是三国中最聪明的人
黄是谁?为什么他是三国中最聪明的人 陈洪范是谁?让吴三桂低头,让秦桧叹息
陈洪范是谁?让吴三桂低头,让秦桧叹息 北魏未平定,宋文帝为什么要杀功成名就的谭道济?
北魏未平定,宋文帝为什么要杀功成名就的谭道济? 盛丰:明朝六位开国公爵之一,但由于怀疑而被杀
盛丰:明朝六位开国公爵之一,但由于怀疑而被杀 既然刘裕是汉室宗亲的后代,那为何刘裕要叫歌名宋
既然刘裕是汉室宗亲的后代,那为何刘裕要叫歌名宋 齐桓公:春秋齐王,春秋五霸之首
齐桓公:春秋齐王,春秋五霸之首 甘龙非常爱他的哥哥。为什么甘龙因为一件小事就拿
甘龙非常爱他的哥哥。为什么甘龙因为一件小事就拿 朱迪造反时,朱允炆为什么不动用他的秘密军队?原因是
朱迪造反时,朱允炆为什么不动用他的秘密军队?原因是